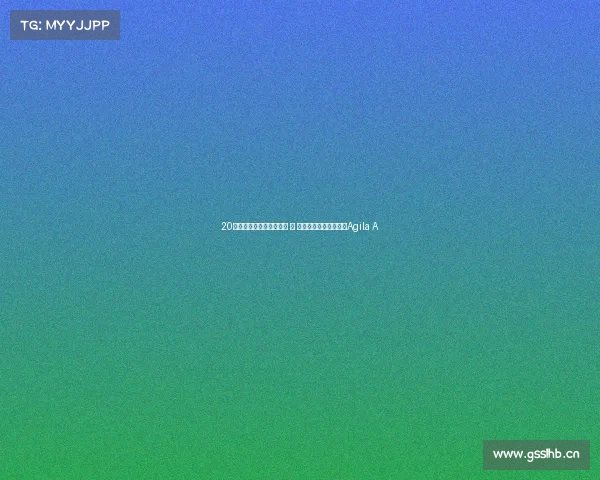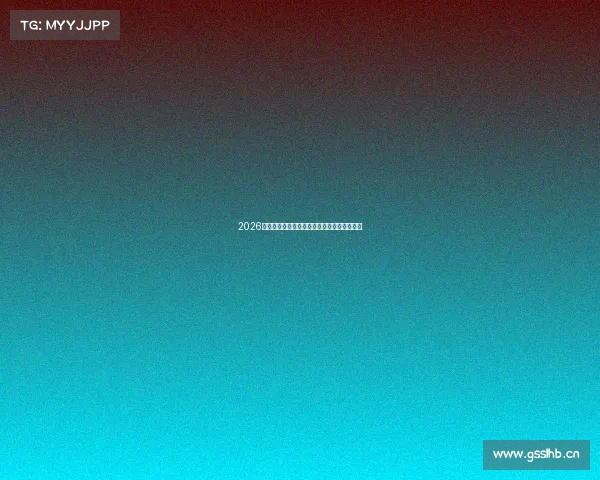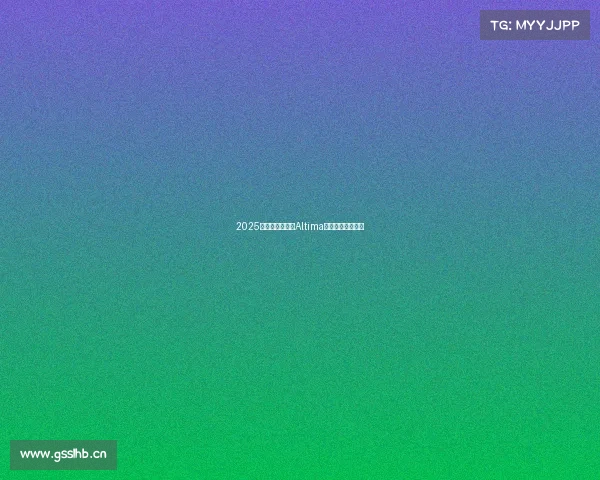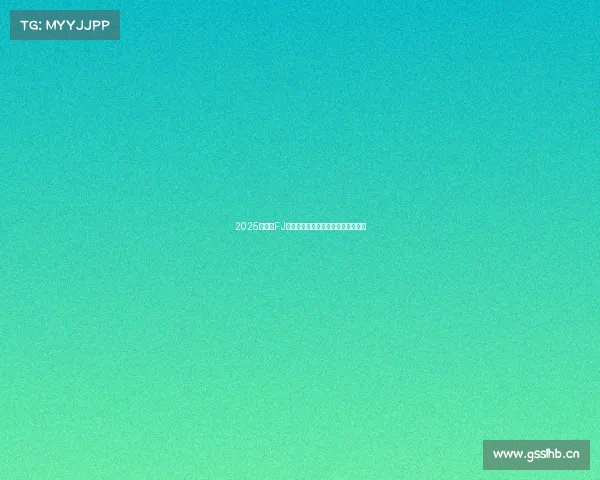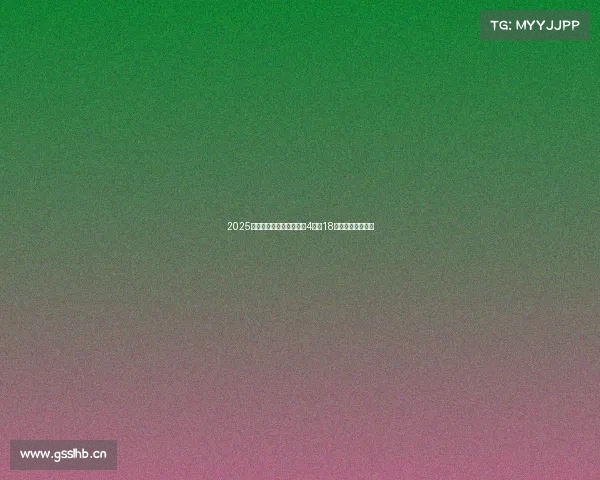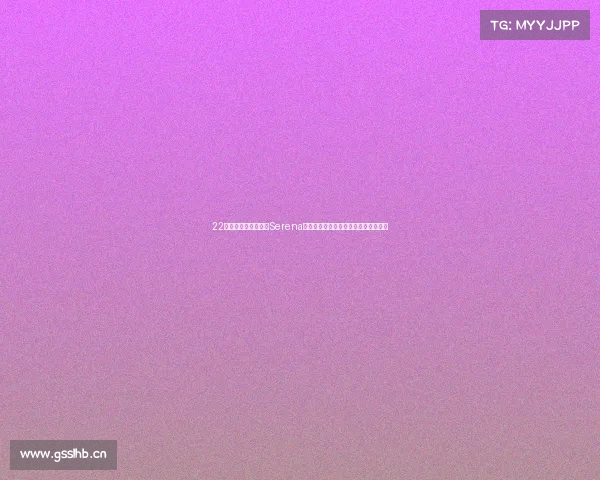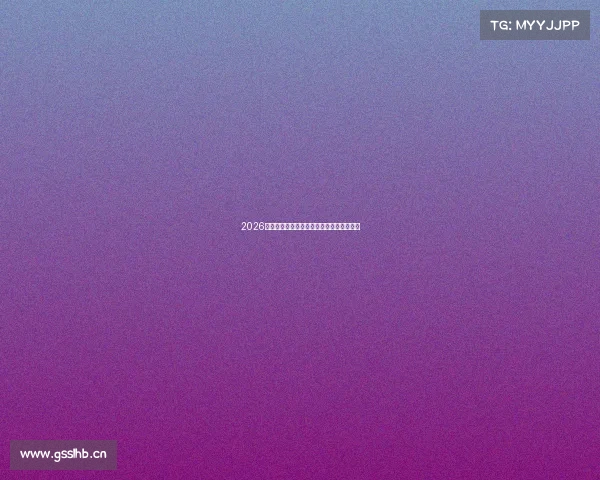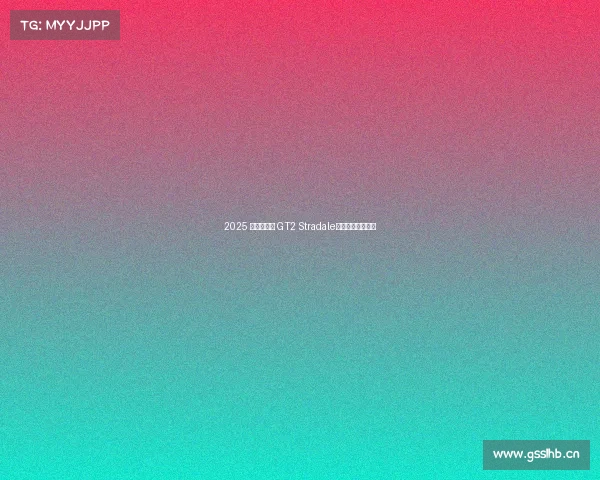当那些伟大时刻到来时,当事人在想什么呢?
当初被问到35秒13分时,麦蒂如是说:“我也不知道怎么赢的。”
乔丹承认过,1982年那决定NCAA冠军的跳投,“球投出去,我都不敢看,我只是拼命祈祷”——但球出手之前发生了什么呢?他也从未提及。
阿伦-艾弗森和雷吉-米勒聊起他们恣肆汪洋的那些时光,会简单回答“篮筐广阔得像大海”。这已经是种幻觉了,但他们投篮时在想什么呢?依然不分明。实际上,大多数回答都是:
“我的脑海里,当时一片空白。”

这个问题,可以有另一个答案。
1992年,约翰-斯托克顿在迈向自己连续第五个助攻王时,却如是说道:
“心理并不重要。球场上没有时间思考。事实上,停下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,只会影响你的发挥。”
同一个春天,乔丹说他有一种“力量之球”的特殊能力。他说他最有统治力的时刻,就必须停止思考,“你必须停止思考。你只需要注意球场上的每个人和他们将要做的事情,然后依靠你的本能。但是有些时候,对方的防守做出你事先没有看到的改变,这时候你就需要自己创造了,这完全是靠本能。”就在此前六年,当记者问他那些空中动作是怎么做出来时,乔丹回答:“我从来没有提前构思过那些动作。”

同一个春天,波波维奇在试图教导大卫-罗宾逊,学会如何不去思考。海军上将的聪明头脑帮助他成为高才生,记住战术和跑位,但阻碍着他发挥杀手本能。
也就在那一年,弗吉尼亚汉普顿的阿伦-艾弗森有了个习惯:赛前想象。这习惯来自于贝泽高中,他的橄榄球教练丹尼斯-科兹洛维斯基先生。他让艾弗森读了本书:麦斯维尔-马尔茨先生1960年出版的《心理控制术》。一个后来艾弗森不断回忆起的细节是,教练指了指他的鞋:“你先把鞋带系好。”艾弗森单膝跪地,双手系鞋带,一面抬头迷惑不解的看教练:“有什么问题吗?”
PC预测“看到了吗?”科兹洛维斯基说,“你系鞋带时,甚至都不需要看自己的鞋?你系鞋带时连想都不用想?对了!我就是要你这么打球,就跟系你的鞋带一样——想都不用想,自动化。在做一件事前,你脑海里先已有一幅图画,然后你就自然操作完成——就这样!”
于是,许多年后,艾弗森习惯在比赛前,想象场上发生的一切,融入其中,然后到了球场上,就自然依照自己的想象行云流水。他不停顿,不思考,依赖着本能流动。

我们可能抵达真相了。
1994年东部决赛第五场,雷吉-米勒第四节轰下25分,五个三分球,屠杀了麦迪逊。赛后奥卡利们后悔不迭:
“他已经意识不到周围的事了。我早该给他一个狠狠犯规,让他清醒一下。”
因为斯托克顿说得对,你根本来不及思考。在篮球场这么个28米长15米宽的地方,半场攻防时大家都挤在一个7米(三分线附近)乘以15米(底线长度)的狭小空间里,十条两米来高、上百公斤重、垂直起跳随便就超过80公分、5秒内跑完40码的怪物,你根本来不及看看想想。你只能依赖本能,跑动、躲避、转身、传、投、跳,间不容发。
所以粗野犯规未必能伤到人,却可以让人醒过来,从“篮筐就像大海”的流畅感觉里醒过来,让已经进入节奏的身体停下来。斯塔克豪斯罚球前一定要蹲一下,邮差罚球前一定要念叨他的儿子,德克罚球前一定要紧紧双腿,然后抬眼看筐——那是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瞄准,而只是如机器流水作业般,重复自己已经做过百万次的动作。从这个角度讲,篮筐后飞舞的客场球迷彩条其实没什么作用,罚球的人几乎已用不到瞄准;反而是皮彭这样“邮差星期天不上班”,可以让他们心里一动——这一动摇,一切便毁了。
魔术师和白巧克力式的“不看人传球”广受好评,但其实某种程度上,NBA的优秀控卫都是在“不看人传球”,只是缺少魔术师那么夸张华丽的指东打西式假动作。我们经常会感叹他们视野宽泛,“背后长眼”。但其实,早在维克森林大学时,克里斯-保罗就承认过,所谓组织后卫的视野,并不在于他们站得多高看得多远。特科格鲁这样的高个子组织者,其实主要占了个子高、传球出手点和角度高的便宜。大多数聪明的控卫,都能在场上跑动时,对周围队友的位置有基本的判断。这是记忆力、训练和本能的结合。所以他们看得见一些几乎不存在的传球路线,我们称之为视野,而他们更多来自本能和感受。
——当然,拉里-伯德宣称他有种能力,在集中精神的时候,周围的一切都会慢下来,于是他能够神出鬼没的传球。当然这更像是显示他有天然的智商优越感,而已。但这不妨碍他恐怖的本能。众所周知,伯德在进入杀气状态时,会呈现截然不同的姿态,比如1981年东部决赛传世的第七场,伯德在一片人仰马翻里捡到后场篮板、推进、擦板中投取得制胜分后,一反此前两年低调沉默的姿态,夸张的挥拳,就像个阴谋得逞的疯子;1984年总决赛第五场,著名的“热之战”,传闻中的35度高温,天勾需要用氧气面罩来维持自己不昏过去,伯德在热浪里砍下34分17篮板,而且当队友ML卡尔过来给他扇风时,伯德两眼血红,直接把卡尔推开了——事后他说自己想不起这一出了。

在这一点上,勒布朗有一个极为恐怖的能力。稍微注意一下他的赛后采访,便能发觉,他能够记得球场上发生的每个动作。2006年在克利夫兰骑士时,他曾经对着《SI》的记者,如数家珍地陈述场上发生的每个球,每次跑位,以及他每次传球的意图——他真能记得。这才是他最被低估的能力。但也因为如此,他偶尔会想多。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最奇怪的现象:当他气势汹汹时(比如2007年东部决赛第五场末尾著名的连得25分,以及2012年东部决赛第六场去到波士顿花园时上半场30分),完全不可阻挡;但他又时常会陷入思索、犹豫乃至于停步不前之中,然后就有了2011年总决赛和2013年总决赛前五场这样的例子。
好的,让我们重新回到球场。
假想你在一个二万人的球场里,声音嘈杂,谩骂和赞美声此起彼伏。
你已经打了两个半小时的球,轻度脱水,心情动荡不安。
你每次进攻只有24秒完成,于是你的精神保持高度紧张。
所以,你自然而然无法想太多,有时甚至头脑过热。许多NBA教练暂停时,都只是在拼命吼“控制篮板、别让它们快攻”这类简单的指令,因为球员们已经疲倦麻木到忘记这茬了,他们需要一点尖锐的声音来刺激大脑,唤醒他们的本能。
我们站在屏幕前,可以靠无限重放来上帝视角,所以觉得某些球明明可以传为什么他们不传。而球员身处其中,根本来不及思考,就这么急速出手了。很大程度上,所谓“投篮有信心”,也无非是出手更直接,少些画蛇添足的调整动作,而已。
1997年总决赛第五场,著名的“发烧之战”,乔丹并没有如通常的英雄姿态般,咬牙切齿客服伤病。实际上,第四节坐在板凳上,他全身是汗,对教练们的问话反应迟钝。但一到场上,他立刻还一记跨步跑投。终场前47秒,乔丹站上罚球线。第一罚得手,双方85平。第二罚,球中前筐弹出。禁区里手纷乱如丛林,乔丹拣到了。皮彭知道乔丹已经无力单挑,自己去禁区要位,背身靠住矮他8公分的霍纳塞克,伸手要球。乔丹把球递了过去。布莱恩-拉塞尔见状,急忙转身,企图包夹皮彭。皮彭回传,乔丹射中关键的三分球,然后平静的往后退。不是他不想庆祝,实际上,他当时不知道自己投进了这球。

“第四节比赛,就在投进导致最终胜利的三分球之前,我几乎要完全脱水了,我开始直打哆嗦,不住地出冷汗。投进最后的那个三分球,我当时甚至不清楚是否投进了,我简直站不住了。”他说。他们什么都不想,听任本能吧他们一路带过意识幽暗的峡谷。
这种平静到麻木的姿态,一如当时麦蒂陈述的“我也不知道怎么赢的”,可能才是最真实的。神话创造者当时在想什么?
——什么都不想。他们许多当事人在当时未必意识得到发生了什么。
——当然也不会想到“安西老师,我要打篮球”,那是艺术夸张……
自然了,他们并不需要意识到什么,只需负责亲自创造不朽;而是在想记住这些,则是我们的责任。